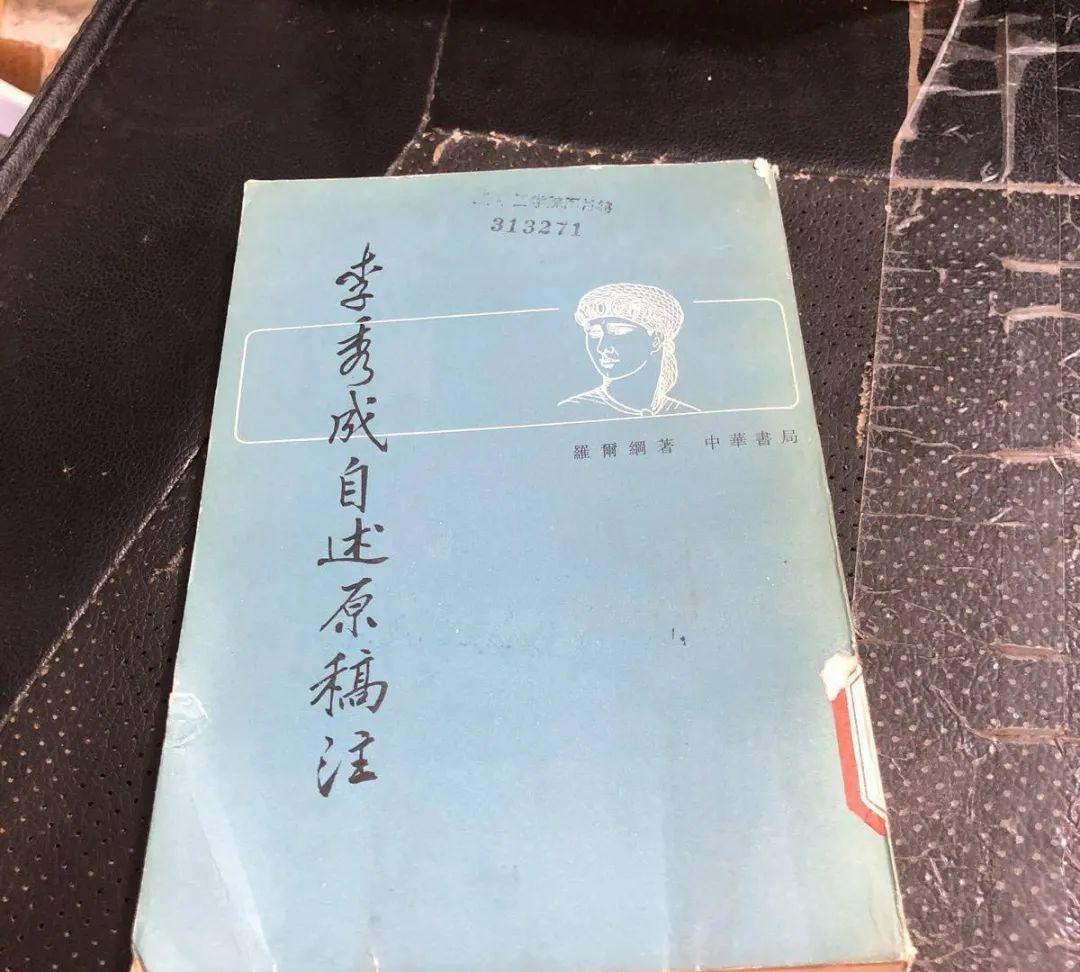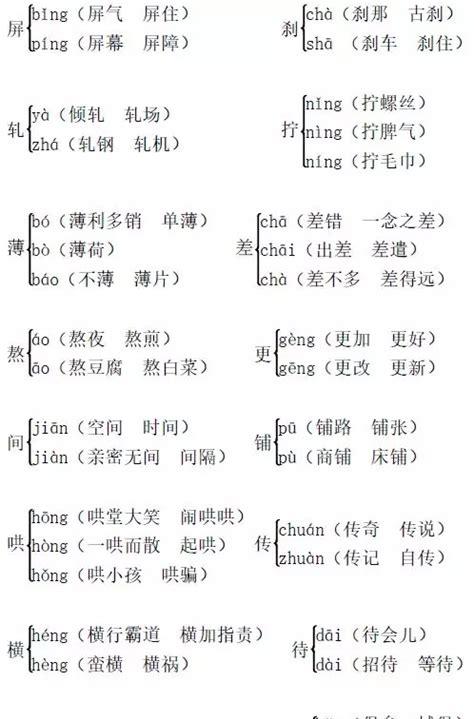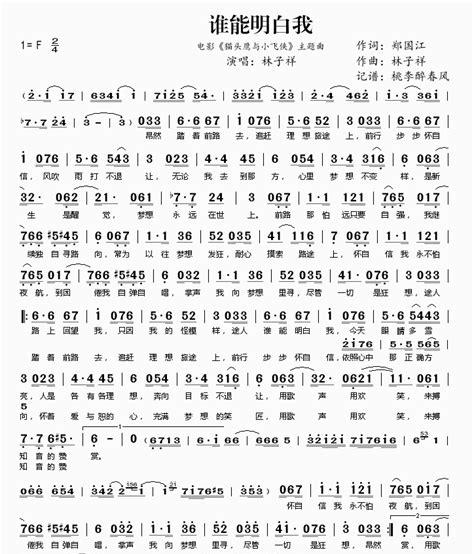情事
倾诉与聆听,城市人的情感故事。
请勿对号入座。
“
现在,上门女婿的称谓已经模糊了,即便有,那也是幸福的上门女婿,仅仅是一种形式而已,不可能会有我们老一辈那种上门女婿改名换姓、命运弄人的事了。
”
口述/夏秋天整理/丁惠忠
我爹的一碗饭几大口就吃下了,小珍站起又帮他添了一碗,而且将饭压实了加满。
●在村庄里,一个男人结婚做上门女婿,入赘女方家,俗称“倒插门”,是一种婚姻生活方式,说不上是好是坏。按传统常理来说,男大当婚,女大当嫁,上门女婿也是始终存在的,这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应该是没有其他选择的选择。我娘就说过,凡是哪家招个上门女婿,村头村尾自然会有闲言碎语,肯定比地上的蚂蚁还要多,不过想想男人讨不上老婆,总比当一辈子光棍强吧。
我在村小学读书时,上学途中必经过一户人家东山墙,听大人说这家老两口养着三个儿子,都已经长成大小伙子,可惜没有女人愿意嫁给他们。我中午放学跑过这段路,经常见这几个儿子在宅前自留地干活,总会嗅到他家杜米栖饭烧焦的味道,以及瞅几眼三四间用芦苇杆扎成芦笆墙做的草屋,就是不见有年轻女人的身影。读初中时,我转到镇上学校念过两年书,家里爹娘再也掏不出钱供我上学,只好书包丢掉乖乖地跟在哥哥、姐姐屁股后面出工挣工分,心里自然惦记着那几位大哥。辍学后那年夏天,有个亲戚来家里跟我爹娘聊起三个儿子那家,大儿子总算结婚了,娶了外村有两个女儿家的大女儿,老二做了那家二女儿的上门女婿,定下好日子,换身干净衣服一个人过去了。这种家属之间婚姻互换关系,在村庄老一辈人群中占有一定比例。隔年,三儿子做了另一家上门女婿。那位我叫她寄娘的亲戚口气软下来,见她悄悄地与我娘说:“我看秋天长大了,人蛮机灵,趁早找个人家姑娘,准不会吃亏。”我娘一声叹气,接着寄娘的话唠叨,意思是家庭遭遇变故,这日子过得不像样子,照这个光景过下去,也只好走他爹这条路。怎么,娘让我做上门女婿?听到她们聊起这个话题,我心里说不出是啥滋味。
●我爹是上门女婿,姓林,传下来的子女都姓娘的姓氏。本来我爹的父母,叫他们爷爷奶奶,娘的父母是外公外婆,我自小两边都叫成爷爷奶奶,潜意识里总感到缺失外公、外婆这两个称呼的。我爹出生于兵荒马乱的年代,他们林家也是大族,在那个村庄里几乎都是林姓人家,但落地不太好,处在江畔荒滩,白晃晃的盐碱地占据大片土地,种子播下去常常颗粒无收,于是在生长野草、芦苇的地方垦荒拓地,才能长一点庄稼,可不够一家老小十几口人塞牙逢呢。穷是一方面,问题在于快到饿死人的边缘,哪有女人愿意嫁到这个村庄?所以这个江畔村光棍最多,生下小孩送给外乡无子女人家寄养的最多,离家走江湖跑码头卖狗皮膏药的人最多,去乞讨拾荒的人最多。解放后,我爹到了三十五岁年纪,仍然没有个女人当家的,怎么办?我的爷爷奶奶听到传言,说几十里外的一个村庄,地势高,熟地,田地长庄稼,有粮食,有饭吃,是个让人有盼头的好地方。做父母的都不愿耽误子女的终身大事,就托人打听哪家有女儿的要上门女婿,不讲女人美丑,只要有地种,有饭吃,有屋住就行。没过多久,那个村庄回话说,有户人家姑娘二十七八岁,倚仗着村庄条件好,自身外貌漂亮,对相亲对象挑走了眼,不想误了婚姻,爹娘为了这个宝贝女儿急得要跳河。那家提出要先看看人,如果看对眼这事好说。
我爹身上带着全家凑的二毛钱,拎着向邻居家借的十只鸡蛋,跟着介绍人去女方家相亲了。尽管是初冬微冷天气,来到女方家,正是中午时刻,赶了几十里路,我爹还是满脸汗水,肚子饿得咕咕叫,再加上介绍人叮嘱守规矩,越临近家门气氛越紧张。这家夏姓人家,一看到我爹高个子,长相端正,浓眉大眼,就是脸黑,身体瘦点,不过一副汗流浃背的模样,倒显出几分大男人的英气来。女方的爹娘满脸笑容,特别是她的娘急忙朝待在西房间的女儿叫唤,“小珍,你快出来,客人到了,去添饭呀”。小珍有点含羞,偷偷地瞄了一眼我爹,转身到厨房捧了两碗菜,返身又端了几样小菜和一盆饭放到客堂间台子上,一齐坐下吃起饭来。我爹的一碗饭几大口就吃下了,小珍站起又帮他添了一碗,而且将饭压实了加满。这个小动作被一桌子人都看见了,介绍人打趣地说:“瞧瞧,小珍心疼人了”。小珍瞪了介绍人一眼,难为情地低下头。我爹当天没有回去,直至三天后帮女方家张罗完婚事,做了上门女婿,才带着小珍回到自己父母那边村庄,算是边报信边看高堂。
●从此我爹改姓夏,两年多时间里,生下我哥、我姐,1953年秋天,爹娘又生下我。家里人口多,开销就大,到我八九岁时,碰上三年干旱、洪涝自然灾害,造成粮食短缺和饥荒,原先这个村庄还算有饭吃,来当上门女婿的男人特别多,被称为上门女婿村。我娘常念叨,像我爹带二毛钱、十只鸡蛋换个老婆的人,是不多的,其他一些上门女婿空手而来,连身上的灰尘都没有,白送给一个女人。村庄里一些上门女婿,由于得不到女方家族的认可,只把他们当成劳动工具使唤,像是从外面牵来的一头牛,只知道把它往大田地赶,根本没有女婿、丈夫、父亲的尊严,甚至没有一个男人应该有的礼仪和地位。上门女婿的家庭,女方好像天生就有一种优越感。村庄北河沿瞿家上门女婿阿杉,得不到半点尊重,他更加自卑,没有一天有过男主人的感觉,瞿家老少都可以欺负他,成了瞿家的长期雇工,他跟几个同是上门女婿的男人说:“怎么一夜天好像回到了旧社会啊!”不管是下暴雨,38度高温,还是寒冬腊月,他是每天被瞿家人催着去干活,即使生病了,连药都不给买,手脚都不让闲下来。阿杉常对外人发牢骚,讨个老婆吃足苦头,早晓得被人这般不待好,还不如不要女人呢。所以,当自然灾害来临开始出现饿死人的困境时,阿杉是第一个离开这个村庄去逃命的,自此再也没有回到瞿家。
我爹虽然没有什么文化,但他懂人情识事务,对夏家长辈关心,小辈爱护,同辈之间多了宽容和理解,各方面都得到了夏氏一族的认可。尤其是三年自然灾害时期,我爹想尽办法与全家老小共同面对,吃野草、啃树皮,按他说的话“连河沟里虾兵蟹将都被翻遍了”,由于干旱,河沟见底,陷在烂泥里的田螺、蚌、芦根等东西,全部进入人的肚子。命总算活下来了,我爹撑起这个家自然受到大家的尊重,其他人家上门女婿都将我爹作为榜样。
●“文化大革命”开始,本来偏远贫困、与世无争的村庄,一下子打破了安静太平的日子。有个在小镇上开缝纫店的小业主,接触三教九流的人多,脑子灵活,观念新,敢于说三道四,被造反派说成是反革命分子,是“特务”。那时我年龄不小了,看到小业主的缝纫店被砸,人也看押起来,就觉得要出事。后来查这个小业主社会关系时,查到了我爹与小业主是老家远房亲戚,他们的父母上一辈之间有些往来,再加上我爹做上门女婿有个好名声,不怀好意者硬是把互不来往不搭界的小辈扯到一起,说我爹是被“特务”安排做上门女婿,潜伏在这个村庄里。还有人揭发我爹帮一个老地主除草,立场不稳,是坏分子。如此一来,我爹被定为四类分子之一。有年开春,在大队院子里,地主分子、富农分子先要将泥地上的草除尽,那天我爹路过看到一个老地主累得摊坐在泥地上,就十分同情他,便上前帮他除草完成任务。因为第二天要召开批斗大会,为了提高春耕生产农民的出工率,以及体现运动的威力,地主分子、富农分子、反革命分子、坏分子等四类分子挂牌站在四方型土墩上,我爹也被列入批斗对象。
●自此以后,我们一家成为别人取笑和斥责,随时可以被人欺负的坏分子家庭。同族人对我爹上门女婿的身份百般刁难,叫他滚回几十路外的老家去,别在他们村庄丢人现眼。我娘抱着我爹边哭边说,提出带我们一家回爹的老家,离开这个是非之地。我爹认真地说:“小珍,到哪里都一样,你相信‘四类分子’哪个是真的?我不能离开,莫须有的‘罪名’迟早会弄清楚的。唉,只是苦了你和孩子们啊!”何止是苦,我奶奶本患有眼疾,现在连人人称道的上门女婿被扣上坏分子帽子,游街批斗,受尽凌辱,奶奶流干眼汨,哭瞎了眼睛,以致失去劳动能力。祖奶奶瘫痪在床好几年,家庭经此打击,病情加重,身边离不得人,亲戚互相帮忙照顾。而我爹既然被列入坏分子队伍,随时被唤去大队种树,除草,开沟垫土,做路,全是没有任何报酬的义务工,回到小队出工还被打折扣。三年自然灾害困难度过来了,到“文革”时期我的家就被一顶高帽子彻底击垮。哥哥、姐姐和我的婚姻,也成了我少年时上学路过那家三个儿子家庭的翻板,哥哥娶了外村女人,姐姐嫁到那家成了外村媳妇。1975年经人介绍,我做了外村一个“四类分子”家庭的上门女婿。我娘说,墙上脏了再涂层泥,反正脏了,怕啥,老天总会开眼的。
●我与人家姑娘玲儿是同病相怜,她没人敢娶,我没人敢嫁,搬到她家住,两个所谓贱民家属就这样一起过着贫贱日子。第二年,好消息从北京传来,“四人帮”被粉碎了,十年文化大革命终于结束了。老天有眼啊,还真让我娘说中了。我和玲儿拎着两瓶酒看我爹娘去了,这漫长的等待总算云开雾散,值得庆祝。公社一纸红头文件把村庄“四类分子”的帽子给撤销了,并在经济上给予一定的补偿。那天我带去的两瓶酒哪里够,哥哥姐姐又从村里商店买了两大缸酒,我们全家和族氏长辈、兄弟个个喝得酩酊大醉。
老话说因祸得福,也许被亏欠太多,大队安排我爹进了村副业场,哥哥到砖瓦厂上班,姐姐被她所在公社安排到棉纺厂上班,生活条件渐渐好转起来。我与玲儿结婚后,因家庭拮据等因素,不想连累孩子,所以没有及时要孩子。到1977年恢复高校招生制度出台,我凭借还有点文化底子,报名参加高考,想以此改变自己和家庭的命运。我妻子发动亲戚、熟人搞来一些复习资料,我胡乱复习、做题,那些文字、数字像是老朋友一般,并没有嫌弃我这个乡村上门女婿,以及曾经所谓的“四类分子”家属,它们都肯帮着我,非常愉快地来到我的脑袋就不走了。几个月后参加公社组织的模拟考试,如果达不到文化考试合格,就取消高考资格。我的文化模拟考试成绩,名列公社报考人数前五名,取得了高考资格。正式考试时,我激动得手抽筋,影响了临场发挥。回家与玲儿一说,她眼泪汪汪地安慰说:“秋天,你过来没有改姓,即便考不上,这个家你是当家人,我们寻别的活路,苦日子都熬过来了,上个学算什么。”高考结果出来,我被当地一座中等师范学校录取了,成为村庄第一个大学生。
两年后毕业,我被分配到外公社当小学教师。这时我与玲儿想要自己的孩子了。过了一年多,我的女儿出生,给家庭带来了新的欢乐。可惜当我和玲儿再想生一个孩子时,实行计划生育政策,只能生一个孩子,我们为女儿办了独生子女证书。现在,我女儿早已结婚,女婿也是独生子女,外孙都五岁了。我们家安排着女儿、女婿的房间,他们两边都居住,方便来往。
现在,上门女婿的称谓已经模糊了,即便有,那也是幸福的上门女婿,仅仅是一种形式而已,不可能会有我们老一辈那种上门女婿改名换姓、命运弄人的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