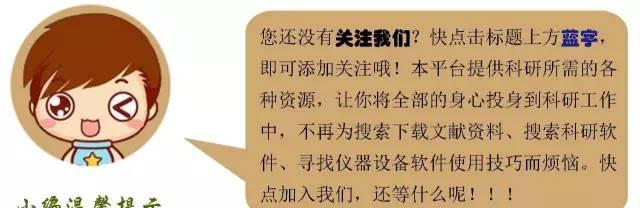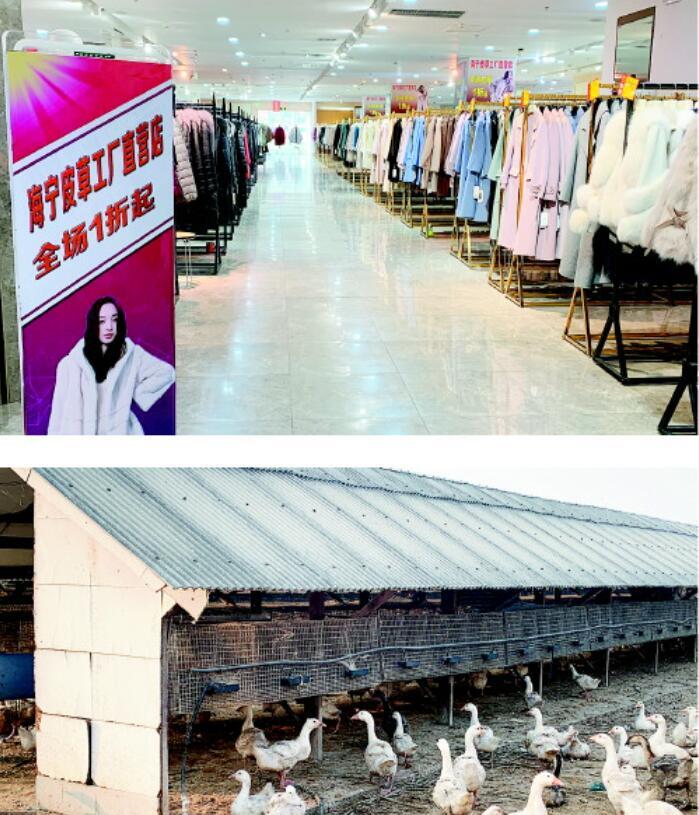△ 在位于四川省广汉市的三星堆遗址5号“祭祀坑”中,考古人员在清理新发现的金面具残片。
1929年,四川省广汉市南兴镇西北鸭子河南岸,偶然被发现的玉石器显露出古老文明的一隅。92年过去,这个被命名为“三星堆”的遗址不断“上新”,大型青铜立人、青铜神树、纵目面具、金杖、黄金面罩、海贝、玉器和象牙……当或是恢诡、或是精妙的出土器物再次重见天日之时,没人能立刻解释清楚这些究竟出自谁手、代表了何种意义。
随着大规模调查勘探和考古发掘工作的不断开展,月亮湾小城、衡量子遗址等重要遗迹,不断明确了三星堆遗址的分布范围和结构布局。和出土器物一样,它们也是人类追溯历史的为数不多的依据,却也因此抛出了一个又一个待解的谜团。
“神秘”成为“三星堆文化”的标签。然而,抛开这些猜测与假说,三星堆的“神秘”之处正是认识、复原和解释历史的关键一环,它促使着人们持续开展考古工作和研究,向答案靠近一步、再靠近一步。
源起何时?

△ 三星堆与世界上古文明暨纪念三星堆祭祀坑发现三十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现场(图片来源:中国考古网)
2016年,为纪念三星堆遗址1、2号“祭祀坑”发现发掘30周年,一场国际学术研讨会在三星堆博物馆召开。国内外100多位文博界的专家学者齐聚于此,针对三星堆的谜团展开了一场又一场的讨论。
现为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三星堆遗址工作站站长雷雨和三星堆考古研究所所长冉红林在会后的综述中提到的第一个话题,即为“年代序列的完善与调整文化性质的再研究”。
彼时学界对三星堆遗址的分期仍有分歧。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孙华曾提出,三星堆遗址分为三期——第一期为龙山时代晚期至二里头文化时代初期,第二期为二里头文化时代晚期至二里岗文化时期(下限可至殷墟第一期前段),第三期为殷墟文化时期第一期(后段)至第三期。前后跨越了龙山时代、夏代及商代三个时期。曾担任三星堆遗址考古发掘副领队、现为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副院长陈显丹则提出了“四期说”。而经这次研讨,年轻的冉红林又继续对原归为第四期的遗存进行细分,提出了“五期说”。
关于遗址分期的争议始终存在。文章指出,这关涉“成都平原进入文明社会之前的社会面貌、族群构成等深层次问题”。直至目前,才基本建立起遗址从新石器时代晚期至西周时期的编年体系和宝墩文化—鱼凫三期文化—三星堆文化—十二桥文化的考古学文化发展序列。

△ 1986年三星堆“祭祀坑”发掘现场。(图片来源:三星堆博物馆)
除去分期的争议,关于这8个器物坑的性质也尚未有定论。在学术论著中,“祭祀坑”通常被打上了引号,孙华认为,这是因为学术界对三星堆器物坑的定性持比较慎重的态度。在三星堆地点还没有完全揭露的时候,对坑的功能本身还要做很多研究,才能做出一个最有可能性的判断。他表示,很多器物的确属于宗教祭祀的像设和器具,但损坏并埋藏却并不一定是出于宗教祭祀的目的。孙华倾向于认为这些坑不是普通祭祀的埋藏,而是某一特殊事件的埋藏。
陈显丹则依然认定这是“祭祀坑”,或者叫“祭祀的埋藏坑”。他解释,不管是金器、铜器还是象牙,这些都是很珍贵的器物,祭祖、祭神或遇到其他重大的事情才能用。火烧这些珍贵器物,就是以器达之于天,也叫作燎祭;再则,坑的方向、形式一致,而且是举行过一定的仪式,有顺序地把东西埋下去,先是小件,然后是青铜器,最上面盖象牙,2、3、4号坑都是如此。

△ 考古人员在三星堆8号“祭祀坑”发掘现场。(图片来源:四川观察)
根据进行中的8号坑发掘情况,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王巍认为,8号坑还发现较多可能与建筑物构造相关的遗迹。比如考古人员发现了3块石板,石板表面平整,疑似建筑物的地面;再比如,坑内有大量较大体积的红烧土块;此前坑内还发现了木头柱子,以及玉石戈都较为集中地分布在一个平面上,“让我们觉得这是一个有意识的行为”,8号坑有可能就是祭祀的神庙遗迹被烧毁之后再整体填埋的。
如此一来,就又延伸出了另一个问题——如此发达繁盛的文明,为何会出现变故,以至消失?目前学界有“洪水灾变说”“权力斗争说”“外敌入侵说”乃至“雷击说”等诸多推测。
王巍表示,他曾跟当地发掘工作人员确认,没有大规模的洪水痕迹,没有淤土,所以起码不是洪水造成。“我个人认为,实际上,是三星堆繁盛一个时期之后,它的政治中心转移到成都的金沙。”他在接受媒体时称,一个重要的证据,就是原来三星堆的年代很宽泛,是距今3600年到3100年,而金沙好像跟它还有距离;但是最新考古测年发现,两者之间是连带、紧密衔接的。所以,有一个衰落、然后兴起的过程。
然而诱发政治中心迁移的因素又是什么?清华大学一团队在2010年发表的一篇论文认为,引起三星堆文明消亡与金沙文明兴起的原因,可能是公元前1099年的一场地震引发了山崩、滑坡,形成堰塞湖并导致河流改道,使流经三星堆的古岷江枯竭,而使都江堰玉垒山出山口水量急剧增大。这也是造成传说中古蜀国罕见大洪水的原因。
以上仅是诸多未解之谜中的一小捧。大到三星堆人和文化的来源去向,与中国既往发现的青铜文化以及古蜀国有何种联系,小到2.62米高的青铜大立人手中握的是什么,为何会具有奇特夸张的青铜艺术、侈丽雍容的金箔技艺和玉石雕琢……人们仍在慎之又慎地破解三星堆遗留下来的谜语。
其难何在?

△ 青铜纵目大面具(摄影:《中国报道》记者 徐豪)
在孙华看来,此前三星堆两个器物坑的器物十分残破,其原本的组合关系、种类数量都不慎明晰,需要进行漫长的修复研究,才能从破碎的信息中发现线索。而在西南交通大学特聘教授、巴蜀方言与文献研究中心主任汪启明眼里,三星堆现在之所以留下这么多“谜团”,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像《华阳国志》这样的文献太少了,”文献不足征“。
成书于东晋时期的《华阳国志》是全方面描写巴蜀历史地理的我国首部地方志,记录的时段从远古到东晋永和三年,涉及大量古蜀时期的历史,汪启明相信,它能为揭开三星堆诸多谜题提供重要参考。
“我国古书亡佚太多。很多我们没办法解释的现象,只是限于当下的文献背景。”汪启明认为,目前考古学上,出土文献一定要和传世文献相结合,才能互为印证,形成完整的解释链条。“目前,各地的博物馆都在找当地的出土器物与三星堆的相似性,这固然是一种解释的办法。但是用这个出土文献去解释另一个出土文献,怎么判断这是偶然的相遇还是同出一源呢?所以无论如何也都还是需要文献的解释。”汪启明告诉《中国报道》记者。
文献的缺失是三星堆研究面临的极大困难之一。四川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巴蜀文化首席专家谭继和曾在文章中写道,“至今我们还不得不主要借助于有关中原文化典籍的知识来认识和探索三星堆遗物及其风貌和内涵”,“这就难免发生歧义,难于准确认识其真谛”。他指出,如“祭祀坑”的命名,也还是来源于中原礼仪知识,因而才引发歧义与争鸣。
除此之外,困难还在于对文献的误读。汪启明以“青铜纵目面具”为例,特别强调“一定要读懂,然后再去发表观点”。该面具的命名源于《华阳国志》中一段记载:“有蜀侯蚕丛,其目纵,始称王。死,作石棺石椁,国人从之,故俗以石棺椁为纵目人家也。”其中明确提到了蚕丛“目纵”。
但汪启明认为,查阅文献后似乎没能发现“纵”字有“突起”之意。就算能理解为“突起”,但“目”字应该是指整个眼睛,三星堆的青铜面具不该是“目纵”,而是“瞳纵”。根据汪启明的猜测,“其目纵”或许是相对于“横”来说——蚕丛的眼睛也许并不是标准的横着,而是有点歪着,还可解释为”目光的延伸“。

△ 三星堆遗址出土陶器刻划符号图录
一方面是现存资料接近空白和误读,另一方面是尚未有新发现的、类似甲骨文等成系统的文字,只是发现了少量不规则的符号。
四川省社会科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李后强在两年前完成主要内容的文章中提出:“我们结合对巴蜀符号印章的研究认为,三星堆发现的符号应是文字的前身,但在发展成系统文字的过程中三星堆文明便毁灭,所以没有形成系统文字。”
“巴蜀符号印章”指的是印面有巴蜀地区特有的图语符号的印章。李后强写道:“巴蜀符号没有来得及演化成表意文字,金沙古城就被洪水和瘟疫所摧毁,就被中原文化、楚文化同化,所以没有形成自己独特的文字体系。”
2010年,时为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副调研员阿余铁日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三星堆文化和古彝族有着深厚的渊源,用古代彝文可以解读很多三星堆神秘符号。
汪启明认为这难以令人信服。他对《中国报道》记者表示,判断是不是文字,是有比较明确的标准的。语言是一种符号系统,是最终把人和动物分开的根本标志之一;而记录语言是文字的基本功能,文字是符号的符号,它需要形音义完备,多地出现,且有一定的上下文,否则很可能就是文字的雏形,即文字画、图画文字或符号文字。单个符号的解释都是一家之言。
对于文化学与文明史研究来说,文字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在汪启明看来,文字可以“解决源和流的问题”,“文字的表意特别确切,通过文字就能知道他们的生活状况,语言状况。很多谜题就能破解”。
3月20日,冉宏林在“考古中国”重大项目三星堆遗址考古成果新闻通气会上透露:“我们倾向于认为三星堆遗址是有文字的。”汪启明认为,三星堆文明的人肯定是有语言的,“比如那么复杂的冶练技术、铸造技术,需要多个工种搭配,也都需要相互沟通”;至于有没有文字,汪启明也更倾向于“有”。他指出,三星堆具备高超的工艺水平,具备文明所必需的城市、冶金、宗教。从《华阳国志》的记载来看,肯定是有文字的。而能否最终确证文字存在,只有仰仗于不断推进的考古发掘。
未完待续

△ 上图为1986年,三星堆遗址考古发掘现场受限于条件,裸露在空气之中,没有被完全封闭保护起来(图片来源:三星堆博物馆);下图为3月10日在三星堆遗址考古发掘现场拍摄的4个大小不同的“考古舱”(图片来源:新华社)
因为新成果的公布,关于三星堆的未解之谜再次被提起,并进入了新一轮的讨论。但与35年前不同的是,在此轮发掘的新坑,有的还没到文物层,但已经出现了没见过的器类种类,且体量非常大。王巍认为,这“会为我们解读古蜀文明提供全新的资料”。
从另一角度来看,不论是科技水平、经济条件还是考古意识,如今都已有了相当大的提高。孙华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1986年时很多现象没有弄清楚,信息不完整,尤其许多有机质文物没有提出去,导致很多信息从挖掘者手中溜掉了。此前诸多基于1、2号坑的研究成果和推测会存在偏差。在全国考古力量的合作和高科技的加持下,过去的一些疑问有望得到解答。
譬如针对年代测定,根据最近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联合北京大学对在三星堆遗址新发现的6个坑的73份炭屑样品,使用碳14年代检测方法进行的分析,初步判定4号坑年代最有可能是在公元前1199年至公元前1017年,也就是距今约3200年至3000年左右。这就印证了三星堆新发现的4号坑碳14的年代区间属于商代晚期。孙华表示,此次采样的标本数量更多,标本选择更恰当;对标本的测量采用了精确度和灵敏度更高的加速器质谱仪,能将误差控制在±25年之内。
旧谜题静待探寻,更多新谜题——诸如丝绸痕迹究竟意味着什么、象牙的来历与意义、生产器物的作坊在哪里、资源与技术是如何掌握的、3000多年前的人们焚烧器物的原因、掩埋器物的时间先后……也逐一浮现。
考古队的目光并非只停留在器物研究层面。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编制的《三星堆遗址考古工作三年行动计划(2019~2022)》,将聚落考古、社会考古作为今后几年内三星堆遗址的主要工作和研究方向。这意味着对三星堆的追问将向着“祭祀坑”群的形成过程、空间格局以及祭祀行为和祭祀体系等行进。按照“考古中国”项目的计划,下一步将继续对新发现“祭祀坑”开展精细考古发掘与文物保护、多学科研究,并在“祭祀坑”的外围勘探发掘,把握祭祀区的整体格局、形成过程,以期系统、全面地把握古蜀文明祭祀体系。
撰文:《中国报道》记者 左琳
责编:何晶
三星堆四号坑碳14年代区间属商晚期(三星堆的两个祭祀坑发现于哪一年)
编辑:昊阳